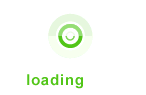徐红亮:爆米花与童年
爆米花和童年本无任何关系,但时代却赋予它们特殊的联系。
几年前的一天晚上,我在出差的宾馆外面闲转悠。远远看到马路边有处火光闪烁,走近后发现,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低头在转着他那爆米花炉子,烧的红彤彤的,热气袭人。
我停了下来,盯着那个烧的通红、肚子圆鼓鼓、不停转动的爆米花炉子,还有炉子后面不停抽拉风车那木然又深沉的老人,顿时就想起“满面尘灰烟火色,两鬓苍苍十指黑”的卖炭翁,还有“独钓寒江雪”的风雪夜归人。
其实,不知道我到底是喜欢上了爆米花的香气四溢,还是怀念童年的那段岁月,总之这一切在眼前让我找到久违的童年。
小时候在我们的村子里,十字街相当于村里的经济、文化中心,如果加上村委会的大喇叭,则也可以称之为政治中心。
这里也是村里人看世界的窗口,这里汇聚着村里仅有的一点点商业气息,以及时尚元素。
货郎,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有?
我们称之为“货郎蛋儿”,也可能是“货郎担儿”,反正这么叫着谁也没有去考究过,更没有必要去考究。“货郎”进村,则必站在十字街摇动那面大一点的波浪鼓——当啷啷、当啷啷;时尚青年(现在都老头儿了)染个头发、换个发型,也必在十字街面晃几圈,为的是传播出去,类似于今天的发朋友圈、小红书,或者发小视频吧!
十字街也是爆米花大爷常常“出台”的地方,其实出台并没有台,一个小马扎,再加上炉子。
孩子们(也就是我们)回家用茶缸子盛来一缸玉米,排上队,等爆米花大爷一一塞到炉膛里,烧啊烧、转啊转,烧好之后,把炉子拿下来矗在地上,用脚使劲一踩,“砰”的一声巨响,本来羞涩的玉米,全都热情奔放,成了名副其实的烫发头。
有时回家舀一缸子玉米,因为跑的快而一路洒了一半的情况也并不少,但尽量不能让爸妈发现,如果发现洒了一路则下次再要玉米难度系数明显加大。
也有不少时候是自己并没有一缸子玉米,而是蹲在爆米花大爷那个长长的布袋子的头儿上“捡漏儿”,就是捡那些蹦出来、漏出来的爆米花,有点像春节时候的捡炮。
爆米花大爷倒也不阻拦,一群垂涎三尺的小屁孩,一切随便!
爆米花大爷可从来不着急,总不急不慢的转动炉子,加火吹风,一个人全搞定了。
当好一通转动炉膛之后,他起身提起炉子,用脚踩头儿上的开关,然后一声巨响,一阵爆米花的香味扑面而来、沁人心脾。
嘿!还有那矫健的身影简直是帅爆了。为了这个矫健的身姿,我差点立志于投身爆米花烹制事业了,当时真是想过“长大我也去炸爆米花”。
现在想起来,仿佛爆米花行业的一大人才损失呢?
时光苍凉的一回眸,跨越的竟是整个时空的巨壑。三十多年了,今年夏天回老家的时候,再去十字街看看,这一切连影子也难以找寻,只是老街仍在,让人仿佛觉得爆米花的香味还在飘溢。
可那风烛残年中的老人,已是斯人远去,或许早已不在人事。不免让人觉得“泪湿春衫袖”的伤感和苦楚!
童年已逝,眼前的爆米花大爷身边已不再有孩子们的欢声笑语、人声鼎沸,也许是那些曾经蹲在炉子边上捡爆米花的孩子们都已经长大、变老,像今天的我。
然而,我的孩子们已无法去感受和体验我童年曾经的快乐了,这是任何PAD和手机所无法替代的。
拎起一包,不扫码、付现金,边走边吃,远远的回望——炉火依旧、简朴依旧,我不知道那些爆米花最终会卖给谁?像我一样的曾经捡漏的孩子?旁边学校的学生们?
这个场景过去好几年了,直到现在我仍然会想起那个灯火昏黄下炸爆米花的老大爷,不禁潸然:谁见幽人独往来,缥缈孤鸿影!